贩卖好故事的聪明人
张悦兴冲冲地把前下属的一篇人物特稿推荐给同事读,推荐完又赞了一嘴。
但辛雯说:这篇文章我看了一半,说实话不喜欢。
这不是她第一次怼张悦了,有时候怼衣着,有时候怼业务,有时候怼做事方式。张悦不介意。张悦是辛雯现在的老板,Figure视频的创始人。在此之前,他是《人物》杂志的出版人及主编,开头力推的那篇稿子正来自《人物》。
《人物》杂志和张悦是彼此生命里的转折点。

1
2012年,《人物》杂志改版,中国新闻界的两位知名记者联手搭档完成了对这本老牌杂志的市场化改造,李海鹏任主编,张悦是执行主编,自此这本新闻杂志以“人是万物的尺度”为价值观。这句话是张悦提的,它来自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的著名哲学命题,也是张悦在大学哲学课堂上听进去的第一句话——对,他毕业于哲学系,他喜欢观察人,然后分析他们。
甫一改版,32岁的《人物》就在2012年年底被《新周刊》评为年度新锐杂志。更多人开始研究这本杂志,以及它的特稿写法——从叙事者、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结构和叙事技巧入手,试图总结归纳人物特稿的叙事策略。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专业主任方毅华认为,它是“人物类特稿研究的绝佳范本”,她亦承认,这个结论的前提是《人物》赢得了受众和市场的高度认可。——改版2年后,《人物》杂志达到盈亏平衡点,不再亏钱。张悦在卷首语里以预估的方式迫不及待地宣布了该消息。
盈利的转机来自杂志2012年底新开辟的短视频业务。当时张悦并没有判断出“纸媒崩塌”的趋势,但他意识到“杂志的性价比更低了”,与杂志人付出的努力和成本相比,读者的重视程度、广告市场的反馈低于预期。他与李海鹏聊起此事时,海鹏亦有同感,做杂志越来越累了。
2012年冬天,张悦开始做人物短视频——他隐隐感觉到把全部精力投在纸质刊物上,并不是一件明智的事。同年,优酷土豆合并;年底时,优酷为移动端访问提供自动适应播放页,视频媒体刚开始探索移动互联网。
《人物》杂志做短视频的优势显而易见:有人物、有故事、有话题。记者采访的时候,视频团队的机器就架在旁边。“第一期视频的传播量已经是杂志发行量的几十倍了。”随时波动的流量显然比沉稳的发行量更让人兴奋,张悦和他的团队开始投入更多精力做新媒体。第一年,人物短视频实现盈利。
此时,一条、二更尚未出现,包括微信小视频。
从产品形态上看,“人物视频”很有机会成为一个现象级的短视频产品,在10万+还算新鲜的年代,《人物》微信公号的图文和视频就有过数条百万+的爆款;一支人物定制视频的价格是7位数;视频产品每年可以为集团带来数百万盈利。
金子发光了。成为一个现象还会远吗?
张悦想花5000块在广点通上试水推广“人物视频”。广点通是腾讯的广告精准投放平台,能帮助人物视频以较低的成本获取更多粉丝关注。张悦要测算这个成本到底有多低。
由于这笔费用与杂志制作无关,属于新产品的推广费用,张悦必须向老板提出申请。除了杂志出版人和主编身份,张悦当时还是杂志所属媒体集团的高级副总裁。为了这5000块,他在2个礼拜里跟老板聊了4次,终于拿到了这笔钱。
过去几年里张悦和资方互相成就,但再开明的资方仍旧身处在行业困局中,经过此事,张悦对于体制和资方的双重束缚下的传统媒体转型,不抱希望了。
这件事、包括离开《人物》后的短暂合伙创业经历,愈发让张悦明确一件事:要做话事人、要做一件自己完全能主导的事情。
2015年,在完成杂志的35周年特刊、阿里巴巴入股集团后,自认为已经完成对这本杂志所有道义责任的张悦裸辞,离开《人物》杂志,他一手创办的视频团队亦陆续出走,不少人去了时尚媒体。言及此,语速飞快的张悦顿了顿,低头按灭烟头,“确实没有办法,我已尽了最大努力了。”

离开《人物》后再创业,张悦身上和身边依然留有这份杂志很重的痕迹
张悦预测,未来的《人物》杂志会以奢侈品的形式存在,依旧是20余人的团队,用媒体人的传统手艺创造价值,但人物视频会是200余人的团队,“这是传统媒体转型的唯一机会”。
辛雯曾两次就职于传统媒体人转型的公司,张悦是她的第三个“转型老板”,她评价张悦是个“相当开放的传统媒体人,思维很灵活,就他这个年纪而言。”辛雯补了一刀后,大笑着说“开玩笑的,他也没有很老”。
2
张悦在人生第三个本命年之前创办Figure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张悦承认自己只擅长和喜欢做内容,《人物》杂志是符合他媒体理想和个人志趣的产品形态,现在他把这种志趣寄托在视频载体上。当时既没有专做人物视频的媒体,也没有张悦看得上的人物视频作品。
Figure要用精神产品链接时代和人。

Figure的办公室在北京市中心,闹中取静。
2017年4月15日,Figure第一支短视频上线。
这不是个好时机。
极光大数据显示,当时的短视频行业用户规模已达1.3亿人。在2016年的井喷式发展后,依然有大批创业者和资本涌入这个行业。张悦开玩笑说 Figure占尽了后发劣势,但这不影响他去融资,他更不会因此妥协、让出部分主导权。
各种创投报道在描述创始人融资时对细节的描述愈发夸张:“第一次见面即谈妥”、“2小时搞定融资”……最后是30分钟、5分钟。 “3分钟可能是最短的。” 问及Figure的融资细节,张悦表示自己确实读到过不少突出这种角度的融资报道,但他并不喜欢拿搞定投资人的时间来衡量创业企业的质量,他话锋一转,“你知道我见徐小平是怎样的吗?”
“我去了真格基金的办公室,徐老师从里面走出来,见到我就握手,身后是他的团队,他一边握手,一边回头示意他的团队。‘张悦,你好,哈哈,欢迎欢迎。你这个项目我们投了,那边办公室准备好了,我现在有点事一会过去,你先跟他们去商量细节。’”张悦当场懵了,准备的一肚子话没说出来。这是他第一次就投融资事宜跟徐小平见面,而关于Figure的项目介绍,张悦只在之前的电话里跟真格副总裁顾三小姐提过。
“(融资)最短记录是3分钟嘛,我是零。So what?”张悦双臂展开,靠在沙发上,幽幽地说。但离那次见面已经一年多过去了,张悦没有做过任何关于项目融资的公关传播,更未从时间纪录的角度去做借势推广。
上一次跟徐小平见面,约是2年前,过程不太愉快。徐小平受邀为“人物视频”拍摄一支定制广告片,但视频拍摄耗费时间太久、要求多且细,徐小平终于忍不了发火了,而处女座的张悦认为花的时间还不够,也不愿意妥协。拍完那个视频,谁也不理谁。直到Figure融资,徐小平换了一个身份看张悦,握手、点头、刷新了自己的投资速度。
在联系真格之前,张悦做了半个月功课,给自己列了一张投资方清单,不到10家。最后他见到了6家,拿到5张TS(投资条款清单),这意味着八字有了一撇。轮到张悦做选择时,他纠结了一下:选人民币基金还是选美元基金?
最后他选了美元——真格基金和贝塔斯曼亚洲投资基金成了Figure的伙伴。“因为内容是跟时间做朋友的游戏。我希望我的合作者能够有远视。”张悦不希望投资人催促创业者尽快变现,打乱他自己的节奏,更不希望资方为了变现,让Figure去做有损于品质的事情。美元基金的退出周期更有耐心,能给张悦更大的尝试空间。
蓓蓓就是看上了张悦这一点:不会随大流、不会改变初衷,“和其他创业者不一样,他对内容品质始终有条线在那儿,你不会担心有一天他为了公司扩张,突然让你去做一件你看不上的事儿。他有媒体人的坚守。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我可能没办法从原来的圈子里出来。”蓓蓓以前是半岛电视台的制片,也做过一个C轮互联网项目的运营负责人,如今在Figure负责“隐秘之事”栏目,这是Figure正在尝试的一条新的栏目化的产品线;她同时还负责国内所有的视频渠道分发和推广。
在Figure之前,蓓蓓就认识张悦,那时候的张悦会在饭桌上用手机玩德州扑克挣点零花钱,他是国内最早的玩家,也是高手。“现在没有了,没怎么见他玩了。他现在压力应该挺大的。”
张悦坦言,现在并没有做杂志累,也不会连续一周睡在办公室,但压力更大了,“身家性命都在这里。”戒了2年多的烟,张悦复吸了。他觉得短视频是疏解城市中产压力和焦虑感的渠道之一,自己却选择把压力留在身边——这个男人抗压能力不弱,目前还没探到自己的底。
3
Figure上线后的第102天,拿了个大奖。
金秒奖的「季度短视频」和「最佳导演」两个重要奖项,并获得唯一一个10万元的现金奖励。

张悦在金秒奖颁奖盛典现场,发表获奖感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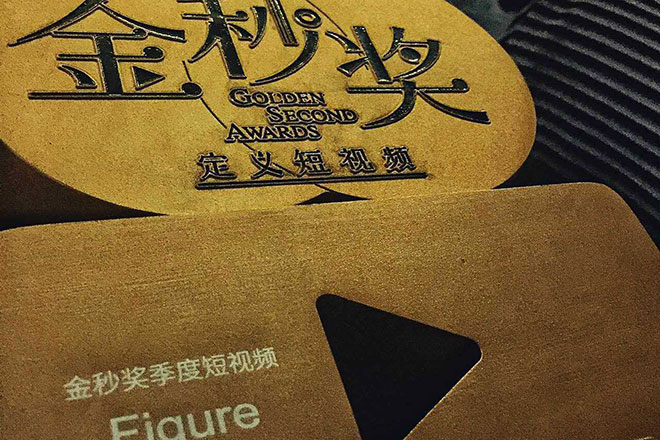
金秒奖奖杯有3.3公斤重,很有“分量”。
金秒奖由今日头条主办,每季度评奖,希望打造成短视频届的奥斯卡。和Figure一同入围二季度评选的短视频团队还包括二更、微在不懂爱、papitube等短视频“老炮”和“网红”。
获奖当晚,Figure宠辱不惊地上线了自己的第32支视频,也是最后一支被贴有“测试”标签的视频。Figure在公号里说,他们离全宇宙最好的短视频又进了一步。
4天后,非测试阶段的第一支正式视频上线,他们采访到了从未接受主流媒体报道、从未露脸的第一游戏主播小智,全网点击播放量超过1700万,是Figure成立以来表现最好的一支视频。
“实际数据可能更高。”辛雯说。她是该片的编导,游戏圈的朋友告诉她,有很多人以各种方式在传播这条视频,比如把视频扒下来,自己写篇文章、按个标题,再传播出去。简言之,在游戏圈、直播圈,这条视频炸了。
仅因为这条片子,辛雯就拿到了1万多块,是目前Figure最高片酬纪录。
但这个片子并不好做。因为辛雯第一次脱离了执行导演去独立做事。
执行导演是张悦为Figure生造出来的一个岗位,是Figure初期的特有产物,和影视圈的执行导演职责不同。
起因在于张悦不要做有传统电视感的产品,他需要人物采访、需要故事深度,就像他反复强调的那样“Figure是一家媒体属性很强的内容公司”,所以他的编导很多来自于资深的纸媒记者,负责采访和故事线架构,譬如辛雯。但麻烦的是,他们起初并不懂镜头语言,于是张悦又招了一些学电影的、做电影的负责画面设计,给他们定的抬头是“执行导演”。在现场,执行导演还可以兼副摄影师。
但辛雯拍小智时,执行导演全都没空。她只能丢掉“拐杖”,硬着头皮上。好不容易拍回来后,又赶上后期人员大调整,这条片子最终经历了5个后期人员才制作完成。
临上线前,辛雯和张悦又争了起来。张悦希望小智视频配的稿子是以人物特稿的形式呈现,但辛雯明确表示时间不够、精力不够。短视频不是正规意义上的调查报道,编导无法核实每条信息来源的真实性,所以做特稿不现实。张悦退了一步,他要求以小标题+自述体的方式编排。
由于稿件文字量极大,辛雯希望采取QA的方式呈现,便于读者检索重点,让尽可能多的人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
两人僵持,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辛雯拉了全公司的同事投票。“最后只有他一个人投自己一票,其他人投我啊。”辛雯眉梢一挑,笑了。
4
辛雯一个月内出了两条近10分钟时长的短视频,她觉得好累。蓓蓓在做运营的同时又在一个月里做了两条片子,她觉得体力到了极限。现在Figure共30多人,每周上线3条视频,张悦认为,每月两条片子是工作效率的底线。他的计划是逐渐组建一个200人的视频团队,Figure实现每日更新。这才配得上它是精神生活陪伴品的使命。

大家都出去干活了,张悦成了“空巢老板”。
但传统媒体人来做短视频,处处受到掣肘。
选题适合视频化吗?一篇人物专访或特稿,短则三四千字,长则万字,同样的故事只给你5分钟时间——全铺上旁白或同期声,也只有千余字,怎么讲明白这个故事?做惯了文字报道的辛雯觉得没办法讲明白,“我不知道5分钟能承受多少。”
在摄像机面前采访当事人,让他毫无保留也是难题。有个被参访对象事后坦言:“他采了我很久,但并没有套出我想讲的话,其实我有蛮多故事。”
每次看到采访录音整理里出现“这个过”、“这个不能讲”时,张悦就不爽了。他知道编导们又没问出东西来,采访对象还没卸下心防。他把自己记者生涯的标准分享给年轻编导——如果问不到自己想要的,他没脸见编辑。
Figure每条视频最后的落版画面都是7个字:好故事不违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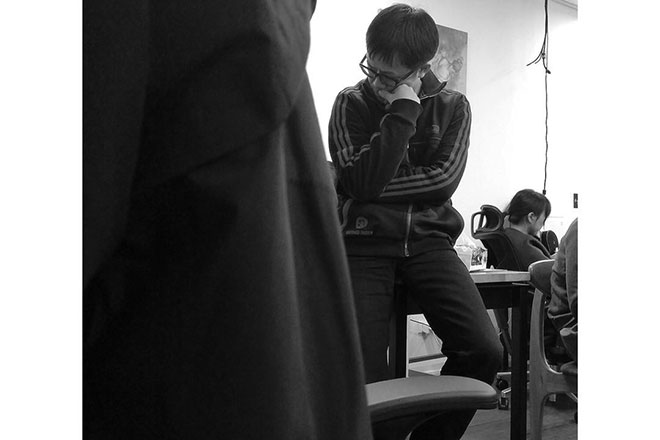
工作中的张悦
张悦知道这个很难,因为用影像语言讲好一个故事,比写特稿不知要难多少倍,“其他短视频都没这么干过,它是非虚构作品,不是写个本子就可以拍。”Figure的短视频是新闻+电影的一种衍生形态。
张悦对好故事有着偏执的追求。他曾拒绝过一家知名企业报价7位数的人物短片拍摄需求。原因是对方提供的人物,不能满足他好故事的需求。在内容上,他要做绝对的王,没有什么能让他低头。
为什么需要讲故事?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童年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这让人着迷、这是刚需、这是人的恒温层。”张悦说。
他是国内一流的特稿记者,善于读人,在《人物》杂志之前,他曾供职于《瞭望东方周刊》、《南方周末》。在一段时间里,他几乎包揽了《南方周末》一半的头版。他对内容的操控力,Figure没人不服。
现在,这个最会写稿子的人桌上堆着《电影镜头入门》、《一个微电影的诞生》、《50 MASTER PHOTOGRAPHERS》、《大师镜头——低成本拍大片的100个高级技巧》等译本。
很显然,这本书没让张悦学会“低成本”这件事。
Figure拍摄一般设2-3个机位,最多时5个;五分钟的视频一般要拍摄3天,素材量达到十几个小时,片比夸张;大量4K的拍摄素材,保存成本极高;视频中所有音乐都付费使用;他还要再招个音编,又正在和全球最大的音乐公司谈版权合作,试图把单次使用成本降低一点儿。
相对于绝大多数短视频制作公司,张悦承认Figure是“铺张”的,无论是财力上还是时间上的投入。他在找平衡点,品质和投入上的平衡点,互联网公司的效率和媒体手艺人的专业之间的平衡点。
所以,Figure看不上行活,看不上那种流水线上下来的、模式化的、批量制造的作品。张悦不止一次在例会上表示,不、要、行、活。他的野心是要做高品格+高传播度的片子,Figure要满足大家对自我审美和形象塑造的需要,Figure要成为受众的自我投射。张悦认为,这种优质作品才具有优质品牌的广告投放价值,因为它具备深度抵达的能力。
辛雯问他:截止目前,哪条片子满足了他“双高”的标准?
张悦想了2秒,答:王兀的片子还凑合。
这支片子的编导就是辛雯,它的全网传播量接近1000万。
几天后,在Figure敞开式的办公间里,张悦给央视资深编导郭嘉又放了一遍王兀的短片,他想听前辈的看法。20年前,郭嘉所在的《东方时空》栏目改变了中国电视语态,成为传奇。
片子很快播完了,郭嘉好一会儿没说话。待她开口时,声音缓缓,小心翼翼:“如果声音线不变,画面换成别的,会是什么效果?…我觉得挺可惜的…”郭嘉情绪昂起来了,“观众要看的是漏洞,是破损。”她觉得王兀的片子太长了,因为里面的信息有重复。如果她来操作,会放上穿帮镜头,把人物置于更大的冲突中。
张悦一直静静地听着。
事后再聊起郭嘉对王兀片子的评价,张悦表示同意,但仍不讳言这条片子给他带来的成就感,“这条片子有它好的一面,郭老师的版本会是另一种好。好是没有止境的,即便我们达到了郭老师的标准,我仍然不会满足。”

张悦不喜欢互联网公司的白色写字板,所以刷了一整面黑板。
不止张悦一个人觉得这条片子好。在Figure八月某周的面试里,10人中有3个是看了王兀的片子过来的。
Figure的片子挺勾人的。
李非凡是大四的学生,他看到Figure拍摄的马可短片时,这个大男孩的胳膊上浮起一层鸡皮疙瘩,李非凡不记得上次这样是什么时候了,这种体验并不常有。随后他翻看了Figure公号里的其他视频,决定要来实习,不作二选。
Figure的实习生都是被片子勾来的,有清华的、有在英国留学的。张悦开玩笑说,Figure实习生的平均线已经水涨船高到伦敦政经学院。——但他并不记得实习生分别来自哪个大学,他说这个不重要。
5
在Figure,坐相也不重要。
在周会上,蓓蓓赤脚盘腿坐在转椅上,跟大家分享上周数据表现;城南抱着抱枕,屁股下是一张椅子,两条腿下又是另一张椅子;张悦微仰,陷在座位里,双腿跷在桌上,夏天的时候光脚,冬天穿着线袜,桌底是一双Birkenstock拖鞋。
蓓蓓和张悦一样,在办公室放两双鞋,一双拖鞋、一双球鞋。“球鞋是备着的。”有一次,一个临时有任务的编导借走了蓓蓓桌底的球鞋。
工作时间喝酒也是被允许的。
Figure的冰箱里啤酒不断。例会迟到的罚款被用来买酒,有员工来了就喝酒。采访对象也喝过Figure的啤酒,然后对着镜头说了金句:“暗恋都不完美,只有说出来才完美。”
挑战张悦也是被允许的。
他不会计较。如果你说的对,他会吸收。“因为我对影像肯定不如我对文字专业,我承认,所以我虚心跟每一个人探讨。但最终我的意见和别人的意见发生不一致的时候,以我的意见为准。”在没有共识的时候,张悦会以自己的方式去试一下。
因为他可以承受失败,他反问,“有什么承受不起的呢?”毕竟这个男人36年来还没输过。
但他很清醒的知道99%的创业公司可能会输,“输了就是我的责任,没有一点借口。”
公司团建玩诈金花时,张悦赢得最多。辛雯评价他有魄力,“他不怕,他有没有好牌他都不怕,他不是那种稳赢的,但他不怕输。比如一晚上他连输五把,最后一把赢个大的,就全回来了。”最后,张悦又把赢到的钱通过奖金返给了同事。
6
Figure微信公号平均每篇文章的阅读量约1万。人物故事的完整文字只在微信公号上呈现——Figure头条号上也尝试放过几篇文字,效果一般。
但9月份上线的视频平均播放量达到了300万。这意味着,Figure的文字只有3‰的受众能看到,编导把精力放在文字上的性价比很低。张悦一方面承认这是为了满足自己这个创始人的纸媒情结,另一方面,他坚信文字的效益会在未来显现。他甚至计划为Figure配上特稿记者,“重量级的采访对象、20分钟时长的片子、哈苏相机拍摄的肖像、以及一篇非常好非常好的特稿。这是我所谓的高配。”
张悦不在乎短视频风口这件事。他做短视频的时候,还没有风口;二次入场的他也不会去追风口。他的目标从来不囿于短视频领域,只是目前专注于此,未来的产品还会包括出版物、纪录片以及电影——事实上,Figure已经是一部明年上映电影的联合出品方。
Figure是个内容公司,它想呈现一场精神产品的盛宴。
但它缺人。它平均每两个月就在微信公号上推送一次招聘信息——欢迎有经验的编导、制片人、商务总监、摄影师,以及纸媒记者。它安慰那些对影像语言感兴趣的文字工作者:“别担心,你的起点和公司CEO是一样的。”

一只第一天来就闯祸的“员工”。
“过来人”辛雯逐渐在丰富她讲故事的手艺,“片子里好多话我没说,但你看完后会自己思考。我觉得文本和影像是两个思考体系。”画面内容、场景选择、剪辑节奏、背景音乐,都能引导观众情绪和认知。她开始留心生活中的各种场景和画面,“逛街、吃饭、打车回家时,看到特别的光影照过来,那一幕很漂亮,我就会记住,用手机拍下来。”——这个聪明人在下笨功夫。
张悦需要这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
在接下来的冬天,Figure可能会扩张到60人,并扩大商业变现的规模。Figure是一个产品,也是时候理解为一个生意了。这个曾经做过中国最挣钱的杂志的男人说:“我一直认为好的商业能让好的内容走得更远。在一个对的赛道,只要能真正能专注做好内容,这件事(生意)就会足够大,大到像时代华纳。”
每条片子上线,负责运营的蓓蓓都会提醒张悦找有影响力的朋友转发,这能带动短片播放量。——张悦很在意每条视频的播放量,这一数据也跟编导的收入挂钩,但Figure坚持在流量数据上不作假,所以朋友的转发是最有效的扩散方式之一。
但张悦意兴索然。骨子里的文人做派又不让他轻易开口,他说好的作品会自己传播。
实在被催得紧了,他也会给关系不错的意见领袖发个消息:
“如果你喜欢的话就转发一下。不强求。”
呵,这个礼貌又骄傲的男人。
来源:24楼影院
相关新闻
